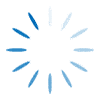意识回笼的瞬间,最先感受到的是冷。
诊疗室恒温的冷气,拂过裸露在外的皮肤。
然后是身下皮质沙发的微凉触感,以及喉咙深处一丝极淡的、若有似无的腥甜。
她没有立刻动。
而是让感官先于意识,一寸寸扫描周身。
头发披散,有几缕黏在汗湿的颈侧。
米白色羊绒裙的领口边缘有一道极细微的、不自然的皱褶,像是被什么力道向侧方拉扯过。
裙摆平整地覆盖着膝盖,但大腿内侧的皮肤,残留着一丝异样的、仿佛被目光长久灼烧过的燥热感。
还有手腕。
左手腕内侧,靠近脉搏的地方,有一小片皮肤泛着几乎看不见的、极淡的粉。
像是被指腹反复按压、摩挲过。
温晚的睫毛几不可察地颤了一下。
她慢慢地、非常慢地,从沙发上坐起身。
动作有些乏力,是深度放松后常见的肌肉松弛,但她的核心绷得很紧。
抬起头。
顾言深就坐在对面的单人沙发里。
姿势和她失去意识前几乎一模一样,长腿交迭,背部挺直,白大褂纤尘不染,袖口一丝不苟地卷到小臂中段,露出那块冰冷的机械表。
他手里甚至拿着记录的笔记本,目光垂落其上,金丝眼镜的镜片反射着纸页的冷光,看起来专注、专业、无懈可击。
仿佛刚才那漫长的一个多小时,他真的只是在观察记录,而非进行任何越界的诊疗。
诊疗室里安静极了。
只有中央空调送风的微弱嘶声,和远处城市隐约传来的、被玻璃过滤后的沉闷车流。
温晚没有开口。
她只是静静地坐着,目光落在顾言深身上,从他一丝不乱的头发,到他握着报告、骨节分明的手指,再到他镜片后低垂的、看不清情绪的眼睛。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。
顾言深翻了一页,纸张摩擦发出轻响。
又翻一页。
他的动作平稳,节奏均匀,甚至带着一种学者特有的、沉浸式的从容。
但温晚注意到,他握着纸张边缘的指尖,因为用力,微微泛白。
终于,顾言深抬起眼,看向温晚。
镜片后的眼睛平静无波,像两泓深不见底的寒潭。
“醒了。”他开口,声音没有起伏,“感觉如何?”
温晚抬起手,指节轻轻抵着太阳穴,眉心微蹙,流露出恰到好处的迷茫与疲惫。
“有点……空。”
“像做了个很长的梦,但记不清了。”
她的声音带着刚醒来的沙哑,柔软,无害。
“正常现象。”顾言深的目光终于从笔记本移向她,镜片后的眼神是专业人士的审慎与疏离,“深度放松状态下,部分表层记忆会暂时模糊。我们这次主要处理了近期因环境压抑引发的焦虑躯体化症状,以及一些潜意识的防御机制。”
他的语调平稳,用词精准,每一个音节都散发着令人信服的理性光泽。
诊疗室里只有他清冷的嗓音,中央空调低微的白噪音,以及温晚略显紊乱的呼吸声。
温晚静静听着,目光落在顾言深脸上,又像是穿透他,落在虚空某处。
她的眼神混沌,像个真正刚从混沌中归来的迷途者。
顾言深继续汇报,指尖的钢笔偶尔在纸页某处轻轻一点,“关于你提到的窒息感,催眠引导显示,其核心并非完全源于物理空间的限制,更多与情感联结的单向输出和反馈缺失有关。你潜意识里渴望的是一种被看见而非被观赏的互动……”
他侃侃而谈,逻辑缜密,分析透彻。
阳光透过百叶窗,在他挺直的鼻梁和薄唇上投下交错的明暗线条,显得他愈发冷静,乃至冷酷。
温晚的视线,却缓缓下移,落在他衬衫的领口下方,锁骨中间的位置。
然后,她忽然极轻微地歪了歪头,唇边漾开一个纯粹到近乎天真的笑容,打断了他的话,声音轻快得像羽毛拂过。
“顾医生,你的领带夹……好像歪了?”
时间,在那一刹那,出现了极其细微的凝滞。
顾言深正在翻页的手指顿住了。
他几乎是下意识地,左手抬起,指尖飞快而隐蔽地探向自己锁骨下方的衬衫面料。
那里平整熨帖,除了温晚刚刚视线停留过的、仿佛还残留着一丝无形灼痕的位置,空无一物。
没有领带夹。
从来没有。
这个动作只持续了不到半秒,快得几乎像是幻觉。
但顾言深全身的肌肉,在那半秒里,绷紧到了极致。
他握着钢笔的右手,指关节因为骤然加大的力道而泛出青白色,笔尖悬在纸页上方,微微颤抖,一滴浓黑的墨迹,无声地晕染开一小团。
诊疗室里死一般的寂静。
窗外的城市喧哗被彻底隔绝。空调的白噪音消失了。
连自己的心跳声,顾言深也听不见了。
他所有的感官,所有的认知,所有的计算,都冻结在那个荒谬的、被轻易戳穿的瞬间。
他像一个站在舞台中央、穿着皇帝新衣的演员,正陶醉于自己完美的演出,却被台下最不起眼的观众,用最天真无邪的语气,轻轻点破了那片虚无。
卑劣。窃贼。伪君子。
这些他从未承认、也从不认为与自己有关的词汇,此刻如同冰锥,狠狠凿穿了他精心构筑的专业外壳。
温晚却仿佛完全没有察觉到他瞬间的僵硬和死寂。
她脸上的天真笑容依旧清澈,甚至带上了一点疑惑,好像只是随口问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。
她的目光轻飘飘地从他空荡荡的领口移开,落回他脸上,继续用那种带着刚醒来软糯的语调问,
“对了,顾医生,你上次推荐的那本关于梦境符号的书,我还没找到。是叫《潜意识之庭》对吗?作者是不是姓荣格?”
她自然地切换了话题,仿佛刚才那句关于领带夹的询问,只是她意识朦胧时的一句无意义呓语,风吹过,了无痕迹。
顾言深依旧僵在那里。
他的大脑还在宕机。
那滴墨迹在纸页上缓缓洇开,像一个不断扩大的、嘲讽的污点。
他抬不起头,也无法继续刚才那套流畅的专业说辞。
温晚那双看似清澈无辜的眼睛,此刻像两面冰冷的镜子,映照出他所有隐秘的、不堪的、骤然暴露的狼狈。
空气沉重得如同实质,压得他几乎无法呼吸。
不知过了多久,也许只有几秒,也许有一个世纪那么长。
诊疗室门外的通讯器,突然发出了嘀一声轻响,随即,助理冷静的声音透过扩音器传来。
“顾博士,下一位预约的李先生已经到了,在休息室等候。”
这声音像一把利剪,猝然剪断了室内凝固的张力。
温晚像是被这声音从某种恍惚中惊醒,她眨了眨眼,脸上的天真和迷茫如同潮水般褪去,换上了一种经过疏导后的、略显轻松却依然脆弱的神情。
她轻轻舒了口气,双手规整地交迭放在膝上,看向顾言深。
“时间到了吗?”她小声说,语气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歉意和依赖,“那下周再见吧,顾医生。”
她站起身,羊绒裙摆垂下,遮住脚踝。
她拿起放在一旁的手包,动作流畅自然,没有再看顾言深一眼,也没有任何多余的表示,仿佛刚才那石破天惊的一句试探和随之而来的死寂,从未发生。
她转身,走向门口,脚步轻盈,甚至带着一点如释重负的飘忽。
手握住门把时,她停顿了半秒,微微侧过头,一缕长发滑过她白皙的颈侧。
“谢谢您,我感觉……好多了。”
声音轻柔,礼貌,无懈可击。
然后,门开了,又轻轻关上。
咔嗒。
一声轻响,将她与这片狼藉的寂静彻底隔绝。
诊疗室内,阳光依旧。
顾言深还坐在那里,姿势与温晚醒来时毫无二致。
只有膝上的笔记本,纸页被钢笔尖戳破了一个小洞,周围晕开那团刺眼的墨迹。
他握着笔的手,因为过度用力而指节惨白,手背上的青筋隐隐浮现。
他维持着这个姿势,很久,很久。
直到助理第二次轻声提醒透过通讯器传来,他才极其缓慢地、僵硬地,抬起了头。
金丝眼镜后的眼睛,望向温晚刚才坐过的沙发。
那里空空如也,只留下一个浅浅的凹陷。
但空气中,似乎还残留着她身上那种清冷的、月光混合初雪的气息,以及……那一丝极淡的、转瞬即逝的、妖冶如彼岸花的、胜利者的余韵。
顾言深猛地闭上眼。
笔,从他脱力的指间滑落,啪地一声,掉在地板上。
滚了两圈,停在阳光照不到的阴影里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